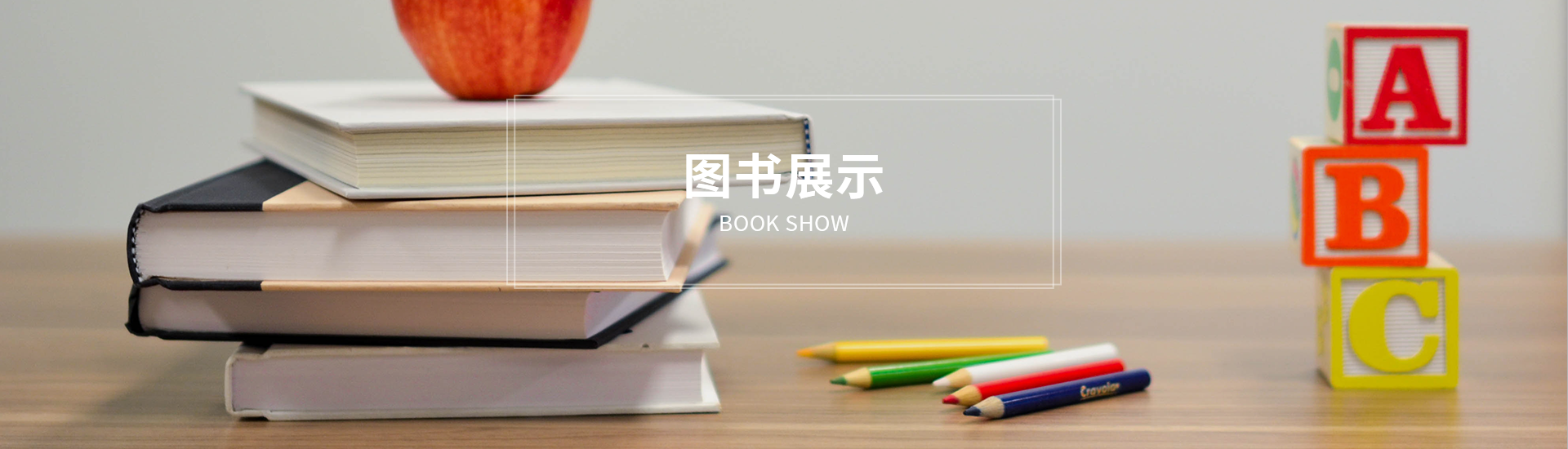一首用百年人生書寫的長詩�����,落下最后一個標點——11月30日上午���,葉嘉瑩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天津市第一殯儀館舉行����。
遺照上的葉嘉瑩,溫柔而純粹��。哀樂低回��,人們深情告別先生�。
一、“何當了卻人間事��,從此余生伴海云”
葉嘉瑩面容安詳地躺在紫色雛菊和白色百合中�����。一朵“蓮花”在她身上盛開��。紅玫瑰作為主花���,擺成心形����。
11月24日��,南開大學講席教授、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�����、中華古典詩詞研究專家葉嘉瑩�,因病醫(yī)治無效在天津逝世。
葉嘉瑩以中國古典詩詞研究為終身事業(yè)��,始終堅持弘揚中華詩詞教育傳統���、傳承中華優(yōu)秀傳統文化,在數十年教學生涯中培養(yǎng)了大批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人才�����,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����、傳承和發(fā)展作出貢獻。
上午10點�,葉嘉瑩先生遺體告別儀式開始。葉嘉瑩的女兒����、頭發(fā)花白的趙言慧靜靜地佇立一旁。
默哀畢,人們三鞠躬�。有人抽泣,俯身叩首�����。人們依次將手中用紫色絲袋包好的蓮子���,輕輕放在葉先生身側�。紫色與蓮子��,都是她生前的所愛����。
華裔女孩張元昕,曾受葉先生詩教精神的感召��,13歲報考南開大學文學院�,并被破格錄取。得知葉先生離世��,她匆匆從就讀的美國哈佛大學趕來�����。放好蓮子,她與趙言慧相擁����。
許多人是自發(fā)前來送別的。在南京工作的王炳洪帶了一本葉先生的書��,一早坐火車到天津����。“是她帶我享受了詩詞之美。雖然她一直不知道有我這個學生����,但我一直認她是我的老師���。”
這些日子���,許多中外高校、協會和學者�����、學生發(fā)來感人至深的唁電����、唁函�。
中華詩詞學會說:“葉嘉瑩先生的逝世是中國文學界的重大損失���。”
中國科學院院士����、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說:“葉先生是詩詞的女兒�����,她的一生是屬于詩詞���,也奉獻于詩詞的�,是最純粹的一生�。”
有網友回憶:“2011年,坐了幾個小時火車來天津����,聽了先生兩場講座。先生八十多歲了仍堅持站著演講��,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����。”
“只為一件事而來�。”葉嘉瑩生前曾這樣描述自己研詩�����、寫詩�����、傳詩的一生���。
臺灣著名作家白先勇曾說:“中國古典詩詞的殿堂是她引我進入的�����。”像他一樣,許多人都是隨著葉嘉瑩的腳步��,走進了詩詞的世界�。
二、“書生報國成何計�,難忘詩騷李杜魂”
“葉先生最后的時光,一直有一種對生命有限的緊迫感�。”作為嫡傳弟子�����,南開大學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張靜20多年來一直伴在葉嘉瑩身邊�,直至最后時刻�����。
“發(fā)現什么好學生了嗎����?”“有誰寫出什么好詩詞了嗎?”這是葉先生在病床上問張靜最多的問題����。
葉嘉瑩一生當了近80年的老師。既給大學生講課��,也給幼兒園孩子教詩�����,帶中國學生領略詩人的生命心魂��,也將詩詞之美傳播到國外課堂�����。
張靜說,最近幾個月葉先生身體更不如前�,但哪怕勉力支撐,也要親自審校在《新華每日電訊》上連載的詩歌講稿�����,“字號到后來越放越大�����,可她看起來實在吃力����,就讓照顧她的護工念。護工斷句不對的地方����,她會等氣力好些時���,認真地給護工講解”����。
她最后的課時,給了護工�����。護工說���,她有幸上了許多堂寶貴的課�。
得知葉先生離世的消息����,臺灣著名導演陳傳興悲痛不已,買了最早的航班從臺灣趕來��。他拍攝的文學紀錄片《掬水月在手》��,留下了葉先生90多歲時珍貴的生命片段����,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。
“通過3年的拍攝�����,我們不斷地接近葉先生����,像是看到一朵花的盛開��。”陳傳興說����,葉先生住院時仍關心著影片在海外的傳播���,“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�����,她將影響更多人�。”
三�����、“遺音滄海如能會���,便是千秋共此時”
葉嘉瑩的百年人生�,見證了國家從離亂到興盛的巨變��,經歷了去國懷鄉(xiāng)���、中年喪女的苦痛�����,曾經輾轉海外�����,最終回歸故鄉(xiāng)�。她始終保持向上����、往前、尋美的達觀����。
“她的生命不僅僅只有詩詞。”葉先生的學生�����、與她結緣半生的南開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陳洪說��,先生興趣廣泛,從文化到歷史�����,從政治�、經濟到物理,“她絕不是‘小閣樓上的人’�����。”
葉嘉瑩的博士生����、研究助理閆曉錚也記得,葉先生與他探討“量子力學”時的認真神情�����。
“她富有真心與童心��。”陳洪說���,葉先生曾喚一群人浩浩蕩蕩去南開大學校園中賞月���,還集齊五位屬鼠的師生拍了一張“五鼠照”���。
葉嘉瑩生前曾說:“我的蓮花總會凋落,我要把蓮子留下來��。”
“葉先生留下了2000多盤授課錄音帶���、200多盤錄像帶和300多盤光碟,以及大量文字稿��。我們會不斷修復����、整理,將先生的精神遺產弘揚好��。”南開大學文學院院長李錫龍說�。
張靜雖滿懷悲痛,前些天卻仍在上課�����。“我想這是先生想看到的����。”
許多南開大學的學生,在用另一種方式悼念他們的“燈塔”。他們在各地參與葉先生十分關心的“詩教潤鄉(xiāng)土”活動���,希望探索出一條促進詩詞文化在鄉(xiāng)村傳播的道路�。
對很多中國人來說��,吟詩甚至要早于識字��。葉先生說:“詩���,讓我們的心靈不死�����。”
素材來源官方媒體/網絡新聞
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